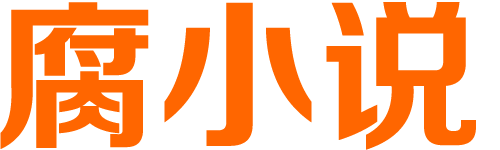(魏晋重生)掌丞天下(二)(6)
作者:月神的野鬼
时间:2017-11-01 08:51
标签:强强
三日后。
王家书房,王导看着坐在对面的王悦,“证词都送到刘隗那儿了?”
王悦点了下头,“送去了。”
“事情办得不错,第一次便能办成这样,确实不错了。”王导执笔在宣纸上写了一个字,“接下来的事便是等了。”
王悦望着王导,过了许久才缓缓道:“父亲,我依旧有些不明白。”
“有何不明白?”
“伪造人证,编弄口供,散播谣言,就只为了让刘隗去给淳于伯伸冤?”王悦看着王导,“这样能成什么事?”
“我问你件事,当初是谁杀了淳于伯?”
“你。”王悦猛地摇头,“不对!你只是调查此事,下令的是皇帝,是皇帝杀了他。”
“若是淳于伯当真有冤,我当然有过错,但谁要背上滥杀的罪名?”
王悦一下子顿住了。
“替淳于伯翻案,便是逼着陛下承认自己滥杀忠良。”王导抬眸看了眼王悦,随意道:“刘隗不了解皇帝,皇帝多疑,又好面子,内忧外患之际,刘隗此时为淳于伯申冤,落在皇帝眼中,他这是拥兵自重趁机威胁自己,大局未定,他尚敢如此,今后不知要多少猖狂。”
所有的迷雾仿佛被轻轻吹开,王悦的眼前忽然清明起来,他一下子抓住了脉络。
“有句古话叫知己知彼,偌大个朝堂,你需要摸透许多人的心思,而最重要的是,”王导望着王悦缓缓道:“你得知道自己在侍奉个什么样的主子。”
王悦有如瞬间醍醐灌顶,他颇为惊叹地看着王导。
王导看着王悦这副样子,笑了笑,他问道:“对了,听说前两日你在街上撞见了谯王世子,他对你动手了?”
“没出事,不过是孩子打打闹闹。”
王导闻声笑了下,“他今日去告了皇帝,说你命人在大街上打他,他揭开袖子,半条胳膊血肉模糊。”
王悦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什么?”
“出倒是没出什么大事,你运气好,皇帝今日顾不上收拾你,不过这段日子你便不要出门了,好好在家反省。”他看了眼王悦,“皇帝的意思。”
王悦觉得司马家真是个个都是厉害角色啊!
司马无忌才十三岁吧?这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厉害!厉害!皇族真是人才辈出!王悦气极反笑,“这种鬼话皇帝也信?”
“是你自己不当心,落人话柄,早告诉你了,把狂妄收拾收拾,无论何时,不要看轻别人。”王导对着王悦道:“行了,下去吧,刘隗一事你已安排得差不多了,这几日观望便好。”
王悦点点头,临走前忽然又问了一句,“这事不会有人起疑吧?”
王导一脸随意,“淳于伯的案子是我经手的,皇帝下令的,若是真的翻案,我与皇帝是一条道上的人,皇帝非但不会起疑,还会更加信我。”
王悦头一次这么佩服王导,由衷的佩服。读书人确实够阴啊。
“下去吧。”
“是。”
待到王悦退下后,王导执笔的手顿住了,不知过了多久,他极轻地叹了口气。
王悦回到自己的院中,他爬上了屋顶,一直坐到了深夜,接连下了几日的绵绵细雨,天有些阴。王悦在屋顶坐了大半夜,心里有些感慨。
他在想一个人,刘隗。
刘隗早年间出身贫寒,一路摸爬滚打上来饱受白眼,他得势之后,处处针对王家人,确切些说,但凡当年得罪过他的人,他都看不顺眼,抓着机会便往死里整,刘隗执掌刑狱时,被他整过的人不计其数,连七八十岁的大臣也不放过。他在建康朝堂可谓是恶名昭彰,听人说,他有一本册子,叫生死簿,上面记录着所有得罪过他的人的名字,按厌恶程度分为三六九等,他每报复一人,便划去一个名字。
心胸狭隘至此,令人叹为观止。
王悦不喜欢刘隗,早些年读书时,也不知是哪位异想天开的仁兄把刘隗安排入了太学,他在太学就已经见识到了刘隗拉帮结派打压异己的手段,这位刘夫子绝对是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背后捅人刀子的事干得那叫一个顺手。能从一介寒生爬到今日的位置,不可能没点手段,刘阎王这称号他实至名归。
王悦曾经想过王导算计刘隗会用什么法子,利用刘隗的自负?还是他的狭隘?但他唯独没想到,王导会利用刘隗为数不多的良善。
刘隗虽然心狠手辣又狭隘自负,可听说故人蒙冤,故人之女沦落至此,在此多事之秋,他仍然挺身而出,只为故人讨一个公道。尽管里头可能有想要往王导头上泼脏水的私心,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做了。
王悦心情复杂。
很小的时候,王导与王敦在堂中下棋,王悦那时候很小,跌跌撞撞地走上前去,王导便把一黑一白棋子塞到他手中,问他,手中的棋子是什么颜色?
王悦说黑是错,说白也是错,最后捏着那两枚棋子坐在堂下哭了一整天。
很多年后,王导对王悦提起此事,说王悦是个不会开窍的人,王悦觉得挺好笑的,你堂堂一个丞相拿这种把戏欺负小孩,你还得意上了?
直到这一刻,王悦才终于明白,在这世上要分出黑白,确实是件很难的事。
刘隗回朝之时,京师大震,百姓夹道相迎。
刘隗进京的第一件事,便是上书请皇帝尽诛王氏,原本还算平静的局势一瞬间又剑拔弩张起来。
上朝之时,刘隗忽然发难,王导当众陈情,说这三十年家国剧变,说君臣立业江东,说得无数人泪洒长襟。
王悦站在王家祠堂中望着那一排排灵位,没有说话。
门阀乱象被人诟病千年,刘隗等人对此恨之入骨,可很少有人想到,若没有琅玡王家,便没有这江东朝廷。史书万卷,堪破了,不过是一句时势造英雄。
乱世汹汹,明主不出,琅玡王家应运而生,待到太平盛世,再看去,乌衣巷,不姓王。
他如今才知道,有些话不必说。
公道并非自在人心,公道自在我心。
王悦一直待在王家禁足,所有的事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事先编好的证词与所谓的证据也都通过淳于伯的旧部一点点摆到了刘隗的面前,果不其然,刘隗在领兵平叛前,他突然上书为淳于伯翻案。
皇帝措手不及,安抚了刘隗之后,立刻下令彻查,真相不过三日便水落石出,淳于伯失职乃是误判,刘隗奏请治丞相王导渎职之罪,请求朝廷将其免官罢职,还枉死的淳于伯一个公道。
正在刘隗步步紧逼、建康流言四起之际,皇帝忽然站了出来,他将此事一并揽在了自己身上,下令勿再牵连旁人。
王导听闻消息,正在与禁足在家的王悦在庭中下棋,他点了下头,待到下人退下后,他对着王悦平淡道:“刘隗大势去了。”
王悦点了下头,“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原以为皇帝会把过错全赖在你头上,可他竟然自己把事担下来了。”
王导忽然笑了下,没说什么,他低声道:“那便是另一件事了。”
“什么事?”王悦追问道。
王导看了眼王悦,轻轻摇了下头,他搁下了棋子,对着王悦道:“近日天好,出去走走吧。”
“我还在禁足期间。”
“呦,何时变老实了?”王导起身拍了下王悦的脸,“行了,刘隗已经去了石头城平叛,你想出去便出去走走吧,别给人瞧见了就成。”
王悦看着王导离开的身影,缓缓地敲了下棋子。
王悦又去了那别院。
推门进去时,司马绍不在院子里,只有一个青衣的婢女陪着淳于嫣荡秋千。
淳于嫣听见脚步声忽然回过头来,原本清亮的眼睛只剩下了一层白布,她却仍是认真地望着,忽然,她慢慢地笑起来,那笑有几分青涩。
王悦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站在门口良久,他终究是没走进去,转身离开了。
淳于嫣抓着秋千的绳索,阳光落下来,柳枝的阴影抚着她的面庞,她将脑袋轻轻靠在了绳索上发呆。
谢家。
苍苍白发的右仆射纪瞻坐在亭子里头,眯眼打量着那盘腿坐在湖边垂钓的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三四岁左右,一大一小,打扮得一模一样,抓着竹竿专心致志地在钓鱼,时不时窃窃私语两句。
纪瞻收回视线,看向坐在他对面的谢景,笑道:“两孩子似乎长大了些。”
“小孩长得快。”谢景给纪瞻倒了杯茶。
纪瞻打趣道:“先是祖仁,又是安石与万石,我瞧你谢家大公子这些年净在家中带孩子了。”
“先生说笑了。”
“我不是说笑,我是觉得可惜。”纪瞻望着谢景,“我一大把年纪了,门生本就不多,就你一个有本事的,偏偏你瞧着最不长进。”
谢景难得轻笑了下,没说话。
纪瞻颇为感慨,忍不住又念叨了一遍,“放眼建康城,将近而立之年,仍未成家立业的,我真找不出第二个了。”他顿了下,“逢君啊,你到底是如何打算的?”
谢景看了纪瞻一会儿,终于缓缓道:“学生已经有心上人了。”
“有心上人那也要……”纪瞻猛地顿住了,抬头刷一下看向谢景,顿时精神了,“你说什么?你有心上人了?哪家的?建康还是江州人士?今年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谢景明显被问得顿了下。
纪瞻忙道:“不要紧!这些都不要紧!说过媒了吗?聘书去下过了吗?事定下来了?打算何时娶进门呢?”
谢景明显又顿了下,过了一会儿才道:“还没有,他……”
纪瞻立刻打断了他的话,“逢君啊,先生七十岁了,先生从前觉着自己活不到你成家的岁数了,如今听你说这些,先生都不知道说些什么!”他喝了口茶平复了一下情绪,对着谢景道:“逢君啊,你听先生说,你年纪轻你不懂,这种事可不能拖啊!愈快愈好!拖着拖着人就没了,咱们这么着,今日先生正好有空,先生替你上门说个媒去,这建康城的官员都愿意卖先生几分面子,咱们今天就把事定下来!”
谢景垂眸看了眼纪瞻激动地抓着自己胳膊的手,顿了下,缓缓开口道:“先生,他和你想的不大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是个男子。”
纪瞻顿住了,他捏着谢景的胳膊看了谢景很久,他慢慢开口道:“没事,没事,谢家子弟众多,你父亲前两日又纳了两房小妾,为谢家传宗接代这事是不指望你的,你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就成,男子也可以,他哪里人士?今年多大?品性如何?”
魏晋龙阳之风盛行,纪瞻淫浸其中多年,年少风流时也曾被英俊的少年爱慕过,他很快缓过来了。谢景的生母死得早,他的父亲又生龙活虎的,外头钓鱼的两个孩子便是谢景的亲弟弟,一个叫谢安一个叫谢万,年纪比谢景小了二十多岁,瞧谢裒这生儿子的劲头,谢家香火肯定兴旺。既然如此,谢景找个男子未尝不可。
纪瞻一辈子大风大浪地走过来,临老了,什么都看开了,人活一世,功名利禄转头空,重要的惜取眼前人。
谢景看了眼看着紧紧抓着自己胳膊不放的纪瞻,开口道:“他琅玡人士,弱冠之年,品性端正。”
纪瞻问道:“既然如此,为何把他领到家里头来?男子虽不用媒妁,却也应当郑重,你和先生说,是谁家的郎君,叫什么名字,先生今日去给你说说。”
“这恐怕是不成。”
纪瞻抓着谢景的手紧了紧,一副谢景今日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他便不撒手的气势,他沉声道:“为何不成?”
“他是琅玡王家的世子。”
纪瞻顿住了。
犹豫了很久,他终于缓缓问道:“王导唯一的嫡子?”
“嗯。”
纪瞻满是皱纹的脸似乎凝住了,接着露出一个恍然明悟的表情,接着又恢复了没什么表情的样子,“琅玡人士,琅玡王家。”他慢慢地收回了抓着谢景的手,“王导的儿子……”
谢景没再说什么,给纪瞻将冷了的茶换了杯新的。
纪瞻望着谢景,“难怪上次央我去给王导说情,你是瞧上了他儿子?”
“上回的事多谢先生了。”
纪瞻看了谢景一会儿,轻声道:“王导他可就这么一个嫡子,嫡长子。”
“我知道。”
纪瞻有些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若是别人也就罢了,王导……”纪瞻沉吟了一会儿,缓缓道“你的根基不在建康,建康城中,琅玡王家的势力盘根错节,你自己当心些,若是真的遇上了什么麻烦,记得同我说。”
“我知道。”
“王导……”纪瞻似乎想到了些什么,低声道:“这两日王家出了不少的事,都说王家要倒,建康年轻一辈的官员是真不知道王导是个什么角色了。”
谢景没说话,颇为赞同。
纪瞻开口道:“你一说琅玡王家,我倒是想起这两日传得沸沸扬扬的淳于伯一事了,你可曾对此有所耳闻?”
“听说了。”
“如今人人都说淳于伯死的冤枉。”纪瞻喝着茶缓缓道:“刘隗他怕是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谢景想起王悦和自己说这事的样子,心沉了下去,也不知王导是如何与王悦解释这件事的。王悦瞧上去倒是真不知道淳于伯一案的真相,连供词都是编出来的,其实哪里需要编什么供词。
淳于伯原本便是枉死的。
当年那一仗,西晋皇帝下令各路人马进京勤王,江东没有及时出兵支援,后来中原沦陷,死了两位大晋皇帝,司马睿与王导为了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将淳于伯推了出去,给他安了个延误水道运粮的罪名,当众斩杀。
淳于伯确实是冤枉的,所有人只当司马睿和王导是为了推卸责任,却没有人深思,当初司马睿与王导究竟为何迟迟没有出兵勤王?
要知道,中原沦陷,愍怀二帝相继身亡,谁会是名正言顺的下一任大晋皇帝?
琅玡王,司马睿。
知道了究竟是谁枉杀了淳于伯,便知道了这到底是件什么样的大事,刘隗犯了个致命的错,错就错在他把这件事儿给捅出来了,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被皇帝放弃了。
如今江左的年轻官员太不了解王导了,瞧王导平日里慈眉善目,竟然真觉得这位筹谋天下的江左宰相真的会是个老好人。殊不知,王导名震后世一千六百年。
谢景捏着杯盏,轻叹了口气。
作者有话要说: 咳咳,在这里,我把两件事串起来写了,一件是刘隗为淳于伯翻案,一件是王敦之乱,真实历史上,先翻案,再造反,我这里压缩了一下,特此声明。
(这章有点乱,但是因为v章字数原因我实在是改不了了……大家先凑合着看吧)
第49章 白玉
刘隗之事告一段落后, 王悦本想去见司马绍, 却不料司马绍自己找上了门,他身边还跟着个司马无忌。
王悦刚开始以为司马绍是替司马无忌打抱不平来了,结果司马绍当着他的面, 扬手便是一鞭子狠狠抽在了司马无忌的身上, 王悦惊得杯子差点脱手。他忙起身打圆场, “太子!太子!你等会!”
司马绍没说话, 扯着司马无忌的肩一把将人拎到了王悦的面前。
司马无忌攥着手良久,低头平静道:“世子,上回的事, 是我的错。”
王悦心道这唱的是哪一出?他忙道:“不用不用!没事!”他看了眼司马绍。
司马绍握着鞭子负手而立, 对着脸色发白的司马无忌道:“站直了!把话再说一遍!”
司马无忌暗自咬牙, 忽然抬头对着王悦大声道:“世子!上回的事, 是我的错!今日是打是骂凭你处置!”
王悦瞧见司马无忌像是要朝他跪下来,立刻伸手扶住了他, “受不起受不起,起来。”他稳稳地扶着司马无忌,回头看向司马绍,“行了, 上回街上那事吧?就小打小闹,我也没放心上,司马绍你快让他起来!”
司马绍这才道:“起来,道谢!”
司马无忌低头片刻,对着王悦道:“多谢世子!”
“行了。”王悦瞧着司马无忌那一肩的血, 扭过头对着王有容道:“带殿下去包扎一下伤口,不知道的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司马无忌低着头没说话,杵在原地不动,直到耳边传来司马绍的声音。
“下去。”
司马无忌似乎颤了下,这才沉默地跟着王有容往阶下走。
王悦瞧得莫名想发笑。
待到两人下去后,司马绍将鞭子往桌案上随手一抛,神色瞧不出喜怒。
王悦回过头,“太子殿下?怎么了这是?”
“上回的事我听说了,拉他过来给你赔不是,他抽了你一鞭子,我如今替你还给他了,你觉得这事两清了没?”
“两清了!两清了!”王悦点点头,“服气!”
都这样了!能不两清?能不服气?
王悦瞧着司马绍那副面不改色的样子,“以前没瞧出来你还会动手打人啊!这一鞭子抽得真狠!我估摸着他此刻真是恨透我了!”
“他之前便恨你,多恨一点少恨一点有何所谓?”
“说的也是。”王悦轻笑了下,慵懒地眯了下眼坐了回去,半晌又道:“你今日上门,只为了让我瞧你打孩子?”
“王敦打到石头城了,皇帝决定御驾出征,朝中事宜全交给了王导。”司马绍打量了两眼王悦,转身往阶下走,“我会与皇帝一块走,知会你一声,建康的事,你帮我照看着点。”
王悦看着说来便来说走便的司马绍,顿住了,他喊住了司马绍,“等会!”
司马绍回头看去。
王悦问道:“你何时走?”
“明日一早。”
王悦闻声顿住了,望着对面的人良久,他忽然道:“今晚我有空,喝酒去吗?”
司马绍微微有些诧异,“你说真的?”
“我何时说过假的?”王悦颇为随意地反问了一句,将脚大咧咧地搁在了桌案上,“走吗?”他望着司马绍的犹豫样子,心中说不感慨是假的,从前连命都敢托付的人,如今却连场酒都不敢喝,世事无常啊。
终于,司马绍点了下头。
王悦笑了起来,却也不像是多高兴的样子,他思索了一会儿,“黄昏时分,城西春风坊,我请了。”
司马绍听见春风坊三个字的时候,下意识多看了两眼王悦。
春风坊,那是当年两人相识不久,王悦带他逛的第一家妓院。他还记得当年他是给王悦抱着腰硬生生拖进去的。
司马绍没应声,算是默然了。
待到司马绍离开后,王悦抬头望了眼天空,此时还不到正午,他想了一会儿,抬手揉了下眉心。
王导说,要想在这朝堂混下去,最首要的,便是你要知道自己侍奉的是个什么样的主子。
那么,司马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主子?
吃过了晚膳,天上又开始淅淅沥沥的飘起雨来,天气颇为糟心。
王悦临出门前,将王有容喊了过来。上回给司马绍撞见他与谢景在一块,他匆匆忙忙地将谢景一个人留在了屋子里,自从这事以后,谢景便对他不冷不热的,说是不理不睬倒也不是,就是有些冷淡,王悦不知道哪里出了岔子,只是隐隐约约地察觉到谢景在压着点什么。
他本来同谢景说了今晚会去谢家,他说的时候,谢景没什么反应,也不知道是听没听见。他如今临时改主意去和司马绍喝酒,思前想后良久,他还是决定让王有容去知会谢景一声。
他把斟酌了良久的话逐字逐句地教给了王有容,王有容一副“包在我身上”的自信样子,他对着王悦道:“世子你放心去,我去同谢家大公子说。”
王悦听完这话,心里头更忐忑了,王有容是王导的人,他与谢景的事王有容并不知情,他有些不放心把这事交给王有容,但交给别人他更不放心了。
最终,王悦还是决定相信他,传几句话而已,能出什么岔子?
王悦安慰了自己一番,出了门。
目送着王悦离开,王有容站在原地摸着下巴,若有所思了一会儿,他转身离开。
谢家阁楼之上,谢景望着雨中的皇城。黄昏时分天地间一片混沌,建康城横卧在秦淮旁,望着那江河无尽滔滔。
侍从走上楼来,“大公子,王家幕僚王有容求见。”
谢景看了那昏暗的雨幕良久,开口道:“让他进来。”
“是。”
王有容拾阶而上,踏上最后一级台阶,他顿住了脚步,望着那背对着自己的世家公子。
“别开无恙,谢大公子。”
谢景端起杯子喝了口茶,没说话。
王有容也不恼,自己走上前去,寻了个淋不到雨又视野开阔的地方站定,“我家世子今晚佳人有约,让我来知会谢大公子一声,说是有什么事,明日再说。”
谢景捏着杯子的手顿了下,抬眸轻轻扫了眼王有容。
年轻的书生站在栏杆前,背靠着满城风雨,不复平日里的怯懦与文弱,一派的从容闲适。
王有容笑了笑,为王悦打圆场道:“我家世子本来是打算过来的,这不是两件事撞上了吗?世子知道后,立刻让我亲自赶过来同谢大公子解释,他确实有点私事来不了了,还望谢大公子海涵。”
谢景直接问道:“他人呢?”
“城西妓院。”
谢景没说话,望着雨中的建康城,缓缓地喝了口茶。
王有容忽然便反应过来,说王悦在妓院不太合适,听上去王悦毁约是为了去风流快活似的,他想着要不要王悦捞一捞面子,抬头见谢景神色如常,他心里定了定,也就懒得去捞了。反正王家世子风流这事建康城家喻户晓,众人早该见怪不怪了。
谢景轻轻放下了手中的杯盏,看向王有容,“说完了?”
“世子交代的事说完了。”王有容对着谢景笑了下,“不过除此之外,我自己另有几句话想同谢大公子说。”
“说来听听。”
“那我便直说了,数年前我曾与谢大公子在豫州有过几面之缘,对谢大公子不择手段的处事风格印象之深,多年后仍难以忘怀。下官不才,说句心里话,这世上能让下官难以忘怀的事真的不多了。”
“是吗?”
王有容看着面前无动于衷的人,不由得想叹气,“下官委实不想与谢大公子过不去,不过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有件事还是想对谢大公子说清楚,王家有地方对不住谢大公子的,丞相自然会还上,还望谢大公子对世子高抬贵手。”
“我若是没记错,是王悦先找上我。”
王有容似乎颇为尴尬,“他忘记了。”
“忘记了。”谢景低低地念了一遍,“所以呢?”
“丞相说了,王家亏欠公子的,他自会补上,此事与世子无关。”
谢景忽然漫不经心了起来,“是吗?”
王有容听见谢景问这两个字时,脊梁莫名感觉到一阵寒意,他有些惊奇地看着谢景,这位是在……动怒?
夜□□临,谢景望着夜雨中昏暗的建康城,目光落在城西的风月场一角。
王有容不知道这位正在想些什么,但凭他的直觉,他感觉谢景现在心情绝对不是很好,这事难得啊!就在王有容犹豫要不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谢景忽然开口了。
“我查过你。”
王有容的神色微微一变,良久才扯出抹笑,“是吗?下官颇为好奇,不知谢大公子查出点什么了?”
“王导之前,琅玡最有名的士族并非王氏,三国时期,琅玡位高权重之人,均是复姓诸葛。”
王有容顿住了,他望着谢景,久久都没说话,终于,他抚掌缓缓笑道:“谢大公子好本事。”
谢景一般不会把话说得太开,除非是一种情况,他动了杀机,他听着楼外夜雨声,抬手轻轻压了下太阳穴。三国末期,中原势力重新分割,无数旧贵族家破人亡,琅玡诸葛氏有一脉后人,因为牵涉入朝堂纠纷而遭灭顶之灾,漏网之鱼逃入了江湖,干起了买卖人头的营生。
谢景放下了手,他没看王有容,而是望着那夜雨秦淮,他没说话。
王悦坐在春风坊里头,和司马绍两人相视无话。司马绍明日一早要随着皇帝出征,他不能喝酒,全是王悦一个人在喝。
说来都没人信,两人就这样大眼瞪小眼地干坐了大半个晚上,谁也没说一句话,最后王悦给这场面逗乐了,对着司马绍道:“我们喊几个女郎进来吧,这不能一点声都没啊,吹笛操琴弹琵琶,好歹有点声啊!”
司马绍点了下头。
不一会儿,屋子里便挤满了莺莺燕燕,丝竹弦声热闹非凡,可王悦与司马绍依旧是谁也没说话,两人对面而坐,在一室的喧哗声中显得格格不入。王悦闲着没事便只能喝酒,一不留神便喝了不少。
两人出门时,王悦抓着司马绍的肩伏在门口吐,吐着吐着忽然笑了起来,他随意地擦了把嘴角的酒渍,仰头问司马绍道:“司马绍,你说实话,你一天到晚心里头究竟在想些什么?”
司马绍滴酒未沾,他知道王悦其实也没醉,王悦能喝多少他心里头有数,他看着王悦,忽然笑道:“你想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
王悦点点头,“想知道,太想了!”
“我想当皇帝。”
王悦愣了片刻,抬手给司马绍用力地鼓了下掌,“大实话!”这话真的太他娘的实在了!他又问道:“为什么想当皇帝?”
“想杀光不顺眼的人,想受万人吹捧,想名垂青史,想干什么便干什么,谁敢拦着便诛他九族。”
王悦瞪大眼看着司马绍,“昏君!”
司马绍点点头,“是又如何?”
“你这人怎么和从前不一样!你从前可是为了天下苍生!”
“那是骗你的。”
“骗我的?”
“不这么说,谁会拥护我?古往今来哪个想当皇帝的不说自己是为了天下苍生?”
王悦目瞪口呆,“等会!你们当皇帝就为了受人吹捧,名垂青史?”
“不,最重要的还是想杀人便杀人,想诛人九族便诛人九族。”
王悦推了把司马绍,忽然笑骂道:“骗子!从前说的全是假话?你就想当个暴君是吧!还想杀人就杀人,谁不服便诛他九族,这么痛快?”
上一篇:(魏晋重生)掌丞天下 (一)
下一篇:(魏晋重生)掌丞天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