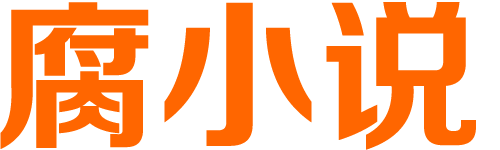(魏晋重生)掌丞天下(二)(2)
作者:月神的野鬼
时间:2017-11-01 08:51
标签:强强
他正想着,身侧的帘子被轻轻揭开,探进来小半个脑袋。
王悦随意地回头看了眼,冷不丁吓了一大跳,“王有容?你装神弄鬼干什么呢?!”
王有容骑着匹白马与王悦的马车并肩而行,他把头伸进去车窗上看着王悦的脸,“世子,有心事啊?”
王悦看着探入马车内的半个脑袋,他就不明白了,王有容一天到晚神出鬼没的怎么没给人当成鬼打死?顿了片刻,他低吼了声,“进来!”
王有容忙不迭地笑了,踢了脚身下的马,马往前蹬了两步,他爬上了王悦停下来的马车,笑呵呵地坐在了王悦身边,“世子,昨晚去谢家为何不带上我啊?这一晚上,下官担心得紧。”说着他便拧起了眉头。
“好了好了,下回带你。”王悦敷衍了一句,“你怎么找过来了?”
“下官心里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世子。”王有容往王悦身边蹭了蹭。
王悦扭头看了他一眼,在那股熟悉的熏香味道中忍不住低头揉了下眉头,“别挤过来!”他低声道:“好了,够了!”
王有容立刻不扭了,坐在王悦身旁静静地看着他,神情恭谨地就跟只王悦养在走廊花架子上的鹦鹉似的。
王悦欲言又止,看着王有容这脸,他觉得心情实在难以平复,“王有容,你别一天到晚跟着我,我知道你奉王导的命令盯着我,但是!你的意图别这么明显!你当我傻子吗?”他看着王有容,脸色微微扭曲,“你克制一些!我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从前一样!成吗?”
王有容隐约感觉到王悦在发火,他忙点点头,屁股往外挪了挪,挪完又往外小心蹭了蹭。
王悦深呼了口气,他迟早给王有容气死,“行了!别磨了!”
王有容闻声一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有些不知道该往自己的屁股往哪里放了,犹豫片刻,他在王悦的跟前蹲下了。
王悦不敢置信地看着他,“王有容你蹲着干什么?”
王有容镇定道:“我觉得蹲着舒服,世子你让我蹲着!蹲着的时候特别舒服!”说着他拍了拍自己的衣摆,示意自己真的很舒服。
王悦瞠目结舌地盯着他,“成。”他点点头,“成吧!”
叫他还能说什么呢?
过了片刻,他问地上蹲得很舒服的人,“荆州那边局势如何了?”
“与几日前传来的消息一致,刘隗与大将军东南对峙,双方都没动静,各州郡也很安静。”王有容看着王悦,小声道:“世子,你别担心了。”
王悦闻声沉默了一会儿。
王有容瞧着王悦的脸色,凑近了些,“世子,你今日瞧着如此之暴躁,又不讲道理,是不是谢陈郡他欺负你了?”
“啥?”王悦扭头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什么东西?”
“没事!”王有容立刻摇摇头,“没事没事!”王有容想起从前在江北与谢陈郡打交道的经历,欲言又止,谢陈郡此人心计之深沉让人记忆尤新,王悦这道行在这人面前玩心眼基本是死路一条,他本来就不太支持王悦去和谢陈郡打交道,若是王悦能自己知难而退,便是最圆满不过。
王有容心里随意地想着,面上依旧挂着讨好的笑,对着王悦依旧不停地嘘寒问暖。
王悦抬手用力地揉了揉眉心,没理会黏黏糊糊的王有容,过了许久才低声道:“你想办法去约温峤出来,我要与他见一面。”
温峤,当年秦淮河上的亡命赌徒,如今已然是太子中庶子,东宫炙手可热的人物。
王悦对太子一党有些成见,但温峤此人除外,这些年王悦混得不如意,温峤那赌徒时常请他去喝酒,一来二去倒是有了些交情,司马绍身边的人,王悦唯独看他顺眼。
温峤此人履历很是传奇,十七岁入仕,年纪轻轻便入了军营,跟着并州刺史刘琨一起镇守北土,彼时正是八王之乱末期,胡人南下,无数汉人浩浩荡荡渡江避难,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衣冠南渡,此时北方几乎全盘沦陷,唯独并州刺史刘琨一人孤悬塞北,温峤跟着刘琨周旋在各胡戎之间,堪堪守住了并州。
温峤当年来江东,便是以刘琨的嫡系身份入朝堂,凭借着并州这层关系,他很快便平步青云,可惜好景不长,刘琨最终死于段匹蝉之手,中原至此彻底沦陷,从此大晋再无北来消息,而温峤便开始了孤身在江东朝堂闯荡的生涯。
到如今,这人也算是闯荡出一方天地了。
当年秦淮河上赌徒依旧在疯狂地摇着赌盅,只不过这次他玩得更大,目光也落在了更远的地方。王悦觉得是时候约这人出来喝杯酒了。
王有容应下了,又问道:“世子,你当真要与太子和解?”他犹豫片刻,问道:“世子可有把握?”
“有没有把握都这样了。”王悦摩挲着手中的玉佩,“我遇刺一事,他心中对我有愧,王家宴会上又瞧见我不人不鬼的狼狈样子,动了恻隐之心,外人不清楚我这些年究竟如何为他掏心掏肺,他自己知道,如今这情分我是收不回来了,不过也别怪我用往日交情算计他。”王悦说着话笑了下,可他没觉得有什么好笑的。
“我早听闻太子心软,也不知是不是真的。”
“称不上心软,但也没有太硬。”王悦点了下头,“放心,江东士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次风波,士族只想看两败俱伤的局面,他们也不会真的看着王家就此倒了的,我们只要稳住司马绍与皇帝,这次便算是挺过去了。”
王悦说得头头是道,王有容认真地听了半天,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思索了半天,他问道:“咦,世子,那陈郡谢氏呢?”这段日子王悦耗在谢家的心血不少,可如今听他的打算,那是要把谢家摘得干干净净啊,那这段日子他们谋划了许多是做什么?
本来拉拢谢陈郡便是瞧上了谢家在豫州与江州的势力,若是不为东南谋划,拉拢陈郡谢氏便毫无意义。
王有容忽然反应过来了,“世子,莫非谢陈郡他不答应?”瞧王悦今日这烦躁程度,这事是没办成?若是谢陈郡拒绝了,那倒是很正常的。王有容忙贴心地安慰王悦,“世子,小小挫折不必放在心上,我们来日方长。”
谢陈郡那算盘珠子的性子,他要是答应得太爽快,反而更让人不安。王有容是这样觉得的,谢陈郡拒绝了,不算件坏事。
王悦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道:“不知根知底的人,用起来不放心,谢陈郡性子难以捉摸,我与他相识时间尚短,再看看吧。”
王有容以为王悦沮丧,便多安慰了他几句,“没事,世子,东南还有大将军在,除了大将军外,还有郗鉴等人,世子不必过于忧心,陈郡谢氏底细不清不楚,拉拢一事本来便不必操之过急,丞相也是这意思。”
王悦点点头,“你言之有理。”他抬手拍了拍王有容的肩,“有道理。”
待到王有容下了马车后,王悦这才缓了神色,他笑了下,过了片刻,他敛去了眼中笑意,低下头缓缓摩挲着那玉佩。
最终,他慢慢将那玉佩抵在了额头上。
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荆州刺史府邸。
沥水的刀锋被青灰色的麻布一点点拭干,露出雪色的锋芒,男人斜坐在榻上缓缓擦着手里的刀,青筋纵横的手稳稳地拂过清亮的刀面,滋啦一声响。
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可瞧上去却不过四十出头的样子,一双亮得出奇的黑色眼睛让他显得很年轻,穿着件武将官服,浑身都是精神气。评断这个年纪的人的很少说外表如何,无论男人女人到这年纪全都是皮松肉弛,谈什么英俊不英俊貌不貌美未免让人啼笑皆非,但这个男人是个例外。
这是个很英俊的男人,哪怕他瞧着年纪大了,可你第一眼见着他,你依旧觉得他很是倜傥英俊,甚至有还有些风流意味。
镇东大将军王敦坐在堂前,灌了一大口江东最贵的茶,随意地喷到了自己的刀上,然后他转着块破抹布随意地擦着自己的刀,堂下站了七八位参将,一时鸦雀无声。
“说说啊!”王敦低声笑了下,“一个个的都哑巴了?”
没人应声。
王敦扫视了一圈,最终视线落在最右的一位年轻将领身上,“钱凤!瞧你平时话多得很,出来!说两句!”
那被点到名的年轻将领上前一步,他沉吟片刻,开口道:“大将军,皇帝先前令谯王司马承刺湘州,后又命刘隗领兵出镇,如今重兵锁境,矛头直指荆州,陛下此举,甚寒荆州将士之心。”
王敦笑了下,“皇帝他想如何便如何,做臣子的如何能说皇帝的不是,皇帝永远没有错的。”
“陛下没有错,当斩的是陛下身旁那群妖言惑众的宵小。古来盛世皆是圣贤辅国,宵小当政,国危矣,如今的建康满是乌烟瘴气,陛下听信小人谗言,远离肱骨之臣,长此以往,民心不复,大晋国之不国!”
王敦望了一眼钱凤,“国之不国?”
“大将军坐镇东南三十余年,身担重任,是江左民心所归。”钱凤朗声道:“此乃社稷存亡之际,大将军身为国家栋梁,当仁不让。”
“当仁不让?”王敦笑着看了眼坐在屏风后头的文弱少年,而后漫不经心地望着眼前的年轻将军,“钱凤,你倒是说说,如何算当仁不让?”
年轻的将军笔直地立在堂前,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诛宵小,清君侧。”
平地一声惊雷,荆州妖风滚烟尘,十万铁骑下金陵。
第44章 杀谁
王悦回了王家, 听闻王敦来了书信, 他茶都来不及喝一口,带着聒噪不休的王有容直奔王导书房。
王导此时人在尚书台,书房里空无一人。
王悦看了眼守卫, 守卫分明是怕了王悦, 在犹豫着拦与不拦时, 王悦当着他们的面推门走了进去。他们面面相觑了一会儿, 没敢说话。
王悦进屋直奔桌案,随意地在案上乱翻了一阵,在王有容一声声“使不得”的惊恐劝说下, 他终于从公文堆中翻出了王敦寄来的书信。
王有容忙道:“世子!拆不得!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要是教丞相知道了……”
“嗯, 知道了。”未等他话未说完, 王悦已经滋啦一声撕开了信封, 抖开了信纸。
差点被话憋死的王有容:“……”
王悦低头认认真真地读完了,沉默了片刻, 他将书信缓缓地又叠了回去,他走到桌案前,忽然低下身翻找了起来。在王有容倒吸凉气的嘶嘶声中,他翻出了这几日王导与朝臣的来往文书, 哗一下摊开便低头读了起来。
王有容就差没双手合十求菩萨保佑王导此时千万别回来。
王悦读完了所有的东西,抬头看向喃喃念经的王有容,问道:“你不是崇尚黄老之术?你求菩萨有用?”
王有容瞧王悦还在笑,气不打一处来,他赶紧冲上前将散落在地的文书啪啪几下收拾后, 又将王悦手中的文书夺过来,“世子!我求求你了!有事我们等丞相回来再议不迟!你可别翻丞相的东西了!”
王悦望着王有容那副样子,无所谓地笑开了,“这算什么?我儿时还在他文书里夹过三文钱一本的春、宫图,他还糊里糊涂地带去上朝了,朝上到一半书还掉了出来,你瞧我也没缺胳膊少腿不是?你怕什么?”
王有容听得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他目瞪口呆片刻,“祖宗!你真是我祖宗!咱们赶紧走吧!”他伸手就去拉王悦,“丞相早说了!没他允许,谁都不许进书房,你不怕死,下官怕啊!”
王悦感觉胳膊被王有容拉住了,他不慌不忙地,反手抓着王有容的胳膊将人一把拽了回来,懒洋洋道:“别急,我问你几件事。”
王有容差点没痛哭流涕,“世子!我求求你了!有事出去说成吗?”
王悦拍拍王有容的肩,示意他稍安勿躁,“我问你,王导这两年一直这样?”
“什么这样?”
王悦扫了下那叠文书,“皇帝对王导这态度从何时开始的?”
王有容看了眼那文书,似乎颇为为难,过了很久他才低声道:“世子,你是丞相的儿子,你还能不知道?”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王悦忽然便沉默了一会儿,他扯出抹随意的笑,“这你还真错了,我的确不知道。本世子这些年活得风光潇洒,每天光盼着自己能去打仗出风头,立大功,朝中这些糟老头子的零碎事如何入得了本世子的眼?”
王有容略显诧异地看了眼王悦。
王悦缓缓道:“我是真的不知。”
王有容顿了会儿,不知道如何安慰王悦,整理了一下思绪,他还是磕磕绊绊地把这两年皇帝与王导之间的事儿跟王悦说了些,他开口道:“这两年陛下忌惮南北士族,朝中许多事都不让丞相插手,大将军多次上书,陛下都敷衍过去了。”
“那王导岂不是很闲?”王悦轻轻笑了下,手随便拿起一份文书,,“看来皇帝也知道王导劳碌命,知道他太闲,便打发他去干些零碎小事,一大把年纪了,还在为朝中官员今年的冬衣操闲心。”
王悦将那文书往案上一递,啪一声轻响。
王有容无奈道:“陛下这两年治理江东,对丞相的‘镇之以静’的政令颇为不满,丞相便不再过问朝中许多事了。”
王悦没说话,过了很久,他忽然笑了一声,“我还记得我儿时,上元节下雪天,皇帝还未登基,微服来王家邀王导去踏雪行舟,他披着白狐裘站在院子里,手里牵着匹白马,王导快步走出去,两人并肩冒着大雪往外走,边说边笑,我伯父回头对着我母亲大声嚷道,琅玡王比他还像王导的血亲兄弟,他说这酒没法喝了,炉边围着的人都笑起来。”
这才多少年过去,便已物是人非到了这境地?说好了契同友执呢?
飞鸟尽,良弓藏。
王悦抚着那文书,许久没听见王有容的声音,一抬头却瞧见穿着官服的王导站在门口,瞧那样子也不知是站了多久了。
王悦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镇定而从容地打了个招呼,“这么早?回来吃饭啊?”
王导看着将脚搁在案上的自家长子,又看了眼一旁面色惨白有如死期将至的王有容,他对着吓坏了的王有容轻轻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先下去。
王有容一个字都没来得及说,马上滚了。
王悦在席子上斜躺着,穿着黑色靴子的脚在案上轻轻晃了晃,他打量着王导,琢磨着他现在立刻跪地抱着王导大腿求饶还来不来得及,还是打死不认把事情全推王有容身上去?王悦正纠结着,王导已经朝着他走了过来。
王导一眼就瞧见了桌案上那封拆开过的书信,问道:“看过了?”
王悦立刻摇摇头。
王导很是淡漠地看着王悦。
王悦马上认怂地点点头。
“信上写了什么东西?看得懂吗?”
“皇帝派刘隗戴渊镇守合肥淮阴,明面上是为了巩固边防,实则是为了对付伯父,伯父给刘隗写了封信,刘隗回伯父一句‘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王敦顿了下,“伯父快气死了。”
王导看了眼王悦搁在案上的脚,王悦刷一下把脚放下了,他冷淡地问道:“你读了十来年书,也算半个读书人,‘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知道这句话是何意思吗?”
王悦明显顿了下,过了一会儿,他缓缓道:“刘隗……刘隗不是鱼,他忘记了道术……他还说伯父也忘记了道术,两人一起忘记了道术,他……他主要想要气死伯父。”王悦点了下头,镇定地看着王导。
王导闻声看着王悦久久都没说话。
王悦点点头,自己附和自己道:“刘隗这人确实不是个东西。”
王导有时候难以相信王悦是他亲生的,这说话的水平确实不像,他盯着王悦看了会儿,王悦这性子很奇特,不像他,也不像曹淑,王悦就像是坊间流传的那种天煞孤星,天生地养,不知道就从哪儿蹦出来了,落在了他头上,便成了他家的天煞孤星。天、煞、孤、星,这四个字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好东西,可王导心里却莫名很喜欢,王家养了一颗天煞孤星,是从天上掉来的,很是珍稀。
王导望着还在琢磨着如何强词夺理的王悦,拂袖在他面前坐下了,淡漠道:“我早警告过你了,不要随意进出书房,更不要把东西带进带出。”
王悦拿袖子给王导抹了下桌子,笑道:“我看外头的侍卫没拦我,我会错意了。”
“王家有谁敢拦着你?”王导打量着王悦的脸色,问了一句,“身上的伤如何了?”
“差不多痊愈了。”
“没再吐血吧?”
“没有。”王悦笑了下,“云叔说了,我身体底子好,好好养几年就养回来了。”
“那就好。”王导点点头,“你没事少往外头跑,好好在家休养,多陪陪你母亲。”
“成吧。”
王导望了眼案上的那堆文书,“翻着什么了?”
“没什么。”王悦低头笑了下,“随便看看。不过话说回来,”他抬头看了眼王导,“皇帝近两年防你防得紧啊!跟防贼似的。你们怎么闹到这地步了?”
“如今江东的局势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南北士族不断壮大,皇帝忧心也是难免。”王导拿文书折子轻轻拍了下王悦的手,“说话当心些!近日不太平,小心祸从口出。”
“知道,我这不是和你一人聊吗?四下又没外人。”王悦偏头望着王导,“我瞧那刘隗很是得意啊,又领兵外镇,又征发各世家大族的僮客,还招揽流民,手都快伸到豫州去了,所以你是真的失宠了?”
王导听笑了,“你对朝中的事不闻不问,对东南的事倒是很清楚啊。”
“所以呢?”王悦一脸好奇,“你真失宠了?”
“养鹰犬玩物才用得上宠这个字,你父亲我这副模样,应当叫失势。”王导微微一笑,“不过你放心,还能凑合供着你,你在外头不必对人低头,该如何猖还是如何猖,王家的门面靠你撑着呢。”
王悦看着王导良久,久久都没说话。
王导瞧着他那副模样,低声笑道:“你怎么了?是怕王家真的失势?放心,我哄你玩的,瞧给你吓的。”
王悦望着王导,一字一句低声道:“父亲我问你件事,若伯父真的被逼反了,事情会如何?”
王导沉吟片刻,开口道:“若真是这样,那你便很可怜了,要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活,谁见了你都会上来踹两脚。”
王悦撑着桌案,缓缓笑开了,“是吗?那还真是难得!”
“谁让你平时得势便猖狂,不收拾你收拾谁?”王导看着王悦那副不成器的样子,一直看了很久,终于叹了口气,“害怕吗?”
“有何好怕的?他们敢杀我吗?”王悦笑了起来,“一群人连杀我都不敢,有何好怕的?”
王导闻声顿了下,他打量着自己的长子,这孩子真的不像他,从长相到气质再到才华,这孩子没有一处是符合他期望的,可唯独这一股烈烈的英气,既不像他,也不像曹淑,仿佛是他自己生来便有的,时常教他耳目一新。
他看着王悦,过了许久才道:“没事就回去吧。”
“好!”躲过一劫的王悦十分识相。
……荆州传来消息的时候,树下的炉子里煎着药,残阳如血,王悦正坐在院中和王有容商量着明日与温峤见面的事宜,侍从直接从门外冲了进来。
“怎么了?”王有容瞧见那通报的侍从慌乱的神色,皱了下眉,“成何体统?”
王悦看向那侍从,“别理他,他中午给王导吓傻了,说,怎么了?”
那侍从扑通一下扑跪在地上,“世子,大将军反了!”
王悦顿住了。
王有容闻声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侍从,嗓子都尖了,“你说什么?”
“大将军反了!”
王悦猛地起身往外走。
深夜,王家大堂前,所有人整整齐齐地坐着,通红的烛光照着在场所有人的脸庞,整个大堂鸦雀无声,只闻蜡烛燃烧的噼啪声响。王悦坐在靠下的一个角落位置,两只手的手指交叉叠着,他沉默地感受着这无声蔓延的沉默。
就在这里,刚刚发生过极为激烈的争吵,他的叔伯们从建康各地赶过来,齐聚一堂,就王敦反叛一事吵得不可开交。
四个多时辰,喧嚣才终于散去,所有人都冷静了下来,他们坐在这堂前沉默地看着夜晚一点点降临,没有一个人敢离开。夜色依旧静谧,可从今夜的黑暗中能依稀嗅到血腥味,荆州十万铁骑的马蹄声一下下落在众人的心头。
有小辈偷偷哭了,王悦听见昏暗的烛光中传来抽泣声,也不知是谁,他扫了一眼,许多人坐在案前,沉默不语,一脸木然。
人心惶惶。
王悦抬头看了眼最上座一直未曾开口的王导。
王导忽然轻轻叹了口气,他拂衣起身,踏过一地的昏暗烛光,朝着外头黑暗中走去。
所有人都看向他。
凌晨的尚书台。
扫地的侍女打着哈欠,拎着水桶走出来,看清眼前的景象的一瞬间,她猛地吓了一大跳,手中的水桶下意识脱手,水桶砰一声落在地上,顺着台阶往下骨碌地飞快滚去。她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
清水溅了一整个台阶,最终沿着石砖缝隙滚到了阶下跪着的男人身边,濡湿了他素色长衫的一角。
天光未明,尚书台阶下跪满了一众素衣的朝官,昏昏沉沉的黑暗中一片鸦雀无声。
所有的王氏族人全都整整齐齐地跪在阶下,笔直着腰,面无表情,面前叠着脱下的官服,官服上压着官印。
那侍女跑到阶下抱着水桶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盯着最前头的那中年男人惊骇得无以复加。
王敦反叛的消息像是一阵风暴席卷了整个江东,十万兵马直扑建康而来,元帝震怒,命刘隗戴渊立即带兵平叛,与此同时,大晋丞相王导率领王氏全族跪在尚书台前,素衣请罪。
武昌点将台,将军亲自击鼓,东风中惊起战鼓第一声响。
扑朔迷离了许久的局势一夜之间明朗起来,迷雾散去,虎狼慢腾腾地露出了獠牙,鹰犬悄悄地睁开了双眼。
那个战袍中卷着沙与血的王家男人腰间别着把秀气的东海刀,他从荆州走来,不久之后,他当着天下人的面,将这个汉人王朝虚弱而软绵的皇权踏了个粉碎。
而在此之前,王悦跪在尚书台前,年轻的皇族太子从他面前走过,他慢慢地低下头去,面色平静。
谢景收着消息其实要比王悦更早一些,他毕竟是在东南待过,得知王导率全族跪在尚书台前请罪的时候,他并没有多少诧异,但他放在案上的手还是下意识顿了下。
王悦的身体怕是受不了。谢景头一次有些后悔,王悦浑身上下全是伤,那天晚上应该克制的。
他的眸光沉了下去。
元帝骨子是个怯懦的人,他担不起事,在当年过江的五位皇族宗亲王爷中,琅玡王家最终选中他,很重要一个原因便是元帝司马睿是个胆怯的人,也正是因为司马睿不是乱世之主的料,他瞻前顾后,果决不足,所以今日他绝不敢真的听从刘隗等人的话趁机灭了琅玡王家。
若是所料不差,元帝面对王敦,愤怒过去后便是恐惧,他会为迅速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他会去找王导。王家人在尚书台前跪不了多久,整件事情由始至终都在王导手里头,从未失控过分毫。
可一直到第三日的中午,王家人全部都还整整齐齐地跪在尚书台下。
谢景不知道王导在想什么,他坐在廊下看着小院,这两日正是倒春寒,外头池水冻得跟深冬似的,风吹在脸上阵阵刺痛。
“送封信去右仆射纪瞻府上。”他终于开口道,声音有些冷。
御书房。
元帝坐在案前看着那份檄文,气得手不住发抖,“笑话!笑话!清君侧?天大的笑话!”他把那份文书对着周顗摔了出去,“他列了刘隗十宗罪!你瞧瞧!僭毁忠良,扰乱朝政!忠良是谁?奸贼又是谁?”
堂下立着的人是义兴周氏的家主周顗,义兴周氏是江东土著士族,在北方士族未曾渡江之前,义兴周氏是江东四大士族之首。周顗作为士族领袖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与王导私交相当不错,他看着皇帝摔下来的那封檄文,低腰慢慢将它捡起来,掸去了灰尘。
“周伯仁你也为王家来求情?”元帝笑着拍了下案上的一摞文书,“瞧瞧!好好睁大眼瞧瞧!全是求情的!缺你一个不缺!”
周顗沉默不语,皇帝还在气头上,满朝文武没人敢来触霉头,只有他这么个老眼昏花的老头犯了浑,可是他不来不行啊,周顗叹了口气,低下腰将散落在地的文书一本本捡起来,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忽然听见脚步声响起来。
“禀陛下,右仆射纪瞻纪大人求见。”
元帝正怒不可遏,闻声忽然一愣,“纪瞻?请他进来。”
周顗一听这名字也有些愣,纪瞻?他回头看去,白发的年迈重臣踏入了御书房,周顗乍一看去有些眼花,定睛一看,竟然真是他!
南士冠冕纪瞻,曾经的东吴士族领袖,这人已隐退朝堂不知多少年了!今日竟然出现在皇宫之中!
周顗相当震撼,他是江东人,对纪瞻的印象不可谓不深刻,东吴四君子之一,当年的“南金东箭”,江东何人不识君?最重要的是,此人在军营中声望极高,如今的江东名士大多沽名钓誉之流,纪瞻名声不显,低调为人,却不知胜过他们多少。在老一辈东吴人的心中,纪瞻便是东吴之国器。
“参加陛下。”年迈的东吴老臣上前一步,微微笑着对着元帝拱手行礼。
“免礼!”元帝忙对着宫人道,“快扶纪大人起来!”他也着实有些意外,当年纪瞻告老辞官,他为了稳定江东人心,亲自上门恳求纪瞻留在朝堂,纪瞻便在朝中挂了个清闲的官职名头,这些年因为年纪大了,纪瞻几乎不曾踏出过府邸大门。
“不知纪大人觐见是所为何事?”
纪瞻像是有些不好意思,哑着嗓子开口道:“陛下,老臣斗胆,今日来为丞相大人求句情。”
话音刚落,不只是元帝,周顗也愣在了当场。
尚书台外。
王悦跪在地上,望着跪在最前头的王导,手终于捏紧了。已经三天过去了,他真怕王导的身体受不了。
王家最多的是老臣,几位叔伯全都已经上了年纪,这样一日日跪下去,每日只喝点汤汤水水吊着条命,这不是个办法。王悦劝不动王导,他也没法劝,这事不是王导能做主的,他们虽说是主动跪下请罪,但皇帝一日不松口,他们便只能跪到死。
上一篇:(魏晋重生)掌丞天下 (一)
下一篇:(魏晋重生)掌丞天下(三)